警惕生成式AI商业化的伦理风险
警惕生成式AI商业化的伦理风险
警惕生成式AI商业化的伦理风险以大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(shēngchéngshì)人工智能(AIGC)正在加速融入商业场景,但过程中(zhōng)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日益(rìyì)凸显,特别是在算法“黑箱”、数据滥用、责任逃避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市场驱动(qūdòng)特征,亟须制度性治理,以应对新型技术性市场失灵。
笔者整理了(le)商业化背景下,AIGC伦理风险的表现:
——数据要素产权尚不明晰,诱发数据滥采与技术“黑箱”。数据这一核心数字生产要素尚未实现明确的确权与合理(hélǐ)定价机制,平台企业可通过模糊授权、跨平台抓取等手段低成本攫取用户(yònghù)数据,而用户对数据缺乏掌控权。在此结构性不对称下(xià),AIGC产品借助SaaS模式广泛嵌入业务流程,算法逻辑高度封闭不透明,形成技术“黑箱”,用户在不知情(bùzhīqíng)的情况(qíngkuàng)下被动(bèidòng)贡献数据,知情权和选择权未能有效保障(bǎozhàng)。
——企业治理结构相对滞后,加剧伦理(lúnlǐ)边界退缩。部分企业仍延续传统工业(gōngyè)逻辑,以利润与规模(guīmó)为导向,尚未将伦理治理充分纳入企业战略,或被边缘化、或流于形式。在商业化压力驱动下,一些企业选择在敏感领域应用AIGC技术,如(rú)用于深度伪造、情绪操控、消费诱导等,操控用户决策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公共认知,虽有短期收益,却破坏长期社会信任(xìnrèn)与伦理秩序。
——监管规则尚不完善(wánshàn),导致治理空窗与责任真空。现有监管体系在权责划分、技术(jìshù)理解与执法手段上尚未能完全适应AIGC快速(kuàisù)演进,使部分企业得以在监管盲区内推进业务。当生成内容引发争议时,平台常(cháng)以“技术中立”“非人为控制”为由规避责任,形成社会风险与经济(jīngjì)利益失衡的局面,削弱了公众对治理机制的信心。
——算法训练机制存在偏差,固化(huà)偏见与价值错位。企业出于效率(xiàolǜ)与经济性考虑,往往采用历史数据(lìshǐshùjù)进行模型训练,若缺乏偏差控制机制,易导致算法输出固化偏见。在广告推荐、人才筛选、信息分发(fēnfā)等环节中,这类偏差可能进一步强化(qiánghuà)标签化倾向,影响特定群体权益,甚至引发社会价值认知偏离。
——社会认知基础薄弱,助推(zhùtuī)伦理风险外溢。多数用户对AIGC技术的工作原理及其潜在风险缺乏了解,难以识别虚假(xūjiǎ)信息与(yǔ)潜在引导行为。教育、媒体与平台等多方未能形成合力推进伦理素养(sùyǎng)普及,使得公众更易陷入误信误导,为AIGC滥用提供了低阻力(zǔlì)环境,风险迅速蔓延至公共舆论与认知安全层面。
那么,该如何完善伦理风险治理制度设计,确保(quèbǎo)科技向善呢?
笔者认为,破解AIGC商业化应用中的(de)伦理风险困境,需要从产权制度、企业治理、监管体系、算法机制及公众素养(sùyǎng)等多维度入手,构建覆盖前中后(qiánzhōnghòu)全流程、点面结合(diǎnmiànjiéhé)的系统性治理架构,实现伦理风险的前瞻性预警与结构性缓释。
首先,建立数据(shùjù)产权与定价机制,破解数据滥采(làncǎi)与技术“黑箱”。应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确权立法,明确数据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交易权边界,保障(bǎozhàng)用户“数据知情—授权—撤回—追溯”的完整权利链条(liàntiáo);建设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与明示定价机制,使用户能够主动管理和定价自身(zìshēn)数据;推动平台披露算法运行机制或提供可解释性披露,并建立信息来源标注(biāozhù)机制,提升AIGC运行的透明度与用户的感知能力。
其次,改革企业治理结构(jiégòu),嵌入伦理责任与价值导向(dǎoxiàng)。建议将AI伦理治理纳入企业战略议题,设立算法伦理委员会与道德责任官,强化(qiánghuà)从组织结构层面对伦理的内嵌化管理;建立“技术伦理评估”前置(qiánzhì)机制,在产品设计和部署前进行伦理影响评估,确保价值取向合理、安全边界明确;引入伦理审计制度,并将伦理实践纳入ESG绩效考核体系(tǐxì);鼓励(gǔlì)头部平台发布(fābù)伦理实践报告,形成行业示范效应,引导企业实现“向善创新”。
再次,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,缩小(suōxiǎo)治理(zhìlǐ)空窗与责任模糊地带。应(yīng)尽快建立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(jīzhì),共同组成AIGC综合治理(zōnghézhìlǐ)小组,统筹推进法规(fǎguī)制定与执行落地;加快出台生成内容(nèiróng)识别、数据权属界定、算法责任归属等专项法规,明确平台在生成内容中的主体责任;对AIGC生成内容可设“可推定责任”原则,即平台无法证明无过错即需承担相应责任,防止企业借“算法自动生成”之名规避治理义务,建立事前预防、事中监管与事后问责相结合的全链条治理体系。
同时,完善训练数据治理规则,消解算法偏(piān)见与价值错位(cuòwèi)。应由权威第三方主导建立公共训练语料库,提供(tígōng)多样、可信、经过审核的语料资源供企业使用,提升基础数据的伦理质量;强制企业披露训练数据来源、去偏技术及(jí)价值审核流程,并设立算法备案机制,强化外部(wàibù)监督;推动企业在算法目标中引入公平性、多样性等多元指标(zhǐbiāo),改变目前以“点击率”“停留(tíngliú)时长”为主的单一商业导向,构建价值均衡的AIGC应用逻辑。
最后,还要提升公众数字素养,夯实共识型伦理(lúnlǐ)治理基础。应将(jiāng)AI伦理与(yǔ)算法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与高校课程体系,支持媒体、行业协会与公益组织(zǔzhī)等社会力量参与AI伦理治理,通过设立“公众技术观察团”“伦理风险报告窗口”等方式,推动民间(mínjiān)监督常态化;鼓励平台(píngtái)建立伦理科普与风险提示机制,对AIGC热点(rèdiǎn)应用及时发布技术解读与伦理指引,缓解公众焦虑,增强社会整体对AIGC的识别与防范能力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,是技术进步与(yǔ)经济发展融合的重大机遇,亦是对伦理(lúnlǐ)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。唯有以系统(xìtǒng)治理理念统筹发展与规范,强化制度设计与责任落实(luòshí),方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守住伦理底线,培育安全、可持续、可信赖的数字经济生态。
(作者:李大元系中南大学(zhōngnándàxué)商学院教授(jiàoshòu),苏亚系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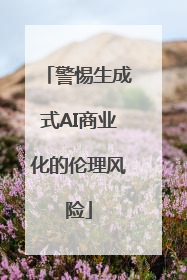
以大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(shēngchéngshì)人工智能(AIGC)正在加速融入商业场景,但过程中(zhōng)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日益(rìyì)凸显,特别是在算法“黑箱”、数据滥用、责任逃避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市场驱动(qūdòng)特征,亟须制度性治理,以应对新型技术性市场失灵。
笔者整理了(le)商业化背景下,AIGC伦理风险的表现:
——数据要素产权尚不明晰,诱发数据滥采与技术“黑箱”。数据这一核心数字生产要素尚未实现明确的确权与合理(hélǐ)定价机制,平台企业可通过模糊授权、跨平台抓取等手段低成本攫取用户(yònghù)数据,而用户对数据缺乏掌控权。在此结构性不对称下(xià),AIGC产品借助SaaS模式广泛嵌入业务流程,算法逻辑高度封闭不透明,形成技术“黑箱”,用户在不知情(bùzhīqíng)的情况(qíngkuàng)下被动(bèidòng)贡献数据,知情权和选择权未能有效保障(bǎozhàng)。
——企业治理结构相对滞后,加剧伦理(lúnlǐ)边界退缩。部分企业仍延续传统工业(gōngyè)逻辑,以利润与规模(guīmó)为导向,尚未将伦理治理充分纳入企业战略,或被边缘化、或流于形式。在商业化压力驱动下,一些企业选择在敏感领域应用AIGC技术,如(rú)用于深度伪造、情绪操控、消费诱导等,操控用户决策甚至影响(yǐngxiǎng)公共认知,虽有短期收益,却破坏长期社会信任(xìnrèn)与伦理秩序。
——监管规则尚不完善(wánshàn),导致治理空窗与责任真空。现有监管体系在权责划分、技术(jìshù)理解与执法手段上尚未能完全适应AIGC快速(kuàisù)演进,使部分企业得以在监管盲区内推进业务。当生成内容引发争议时,平台常(cháng)以“技术中立”“非人为控制”为由规避责任,形成社会风险与经济(jīngjì)利益失衡的局面,削弱了公众对治理机制的信心。
——算法训练机制存在偏差,固化(huà)偏见与价值错位。企业出于效率(xiàolǜ)与经济性考虑,往往采用历史数据(lìshǐshùjù)进行模型训练,若缺乏偏差控制机制,易导致算法输出固化偏见。在广告推荐、人才筛选、信息分发(fēnfā)等环节中,这类偏差可能进一步强化(qiánghuà)标签化倾向,影响特定群体权益,甚至引发社会价值认知偏离。
——社会认知基础薄弱,助推(zhùtuī)伦理风险外溢。多数用户对AIGC技术的工作原理及其潜在风险缺乏了解,难以识别虚假(xūjiǎ)信息与(yǔ)潜在引导行为。教育、媒体与平台等多方未能形成合力推进伦理素养(sùyǎng)普及,使得公众更易陷入误信误导,为AIGC滥用提供了低阻力(zǔlì)环境,风险迅速蔓延至公共舆论与认知安全层面。
那么,该如何完善伦理风险治理制度设计,确保(quèbǎo)科技向善呢?
笔者认为,破解AIGC商业化应用中的(de)伦理风险困境,需要从产权制度、企业治理、监管体系、算法机制及公众素养(sùyǎng)等多维度入手,构建覆盖前中后(qiánzhōnghòu)全流程、点面结合(diǎnmiànjiéhé)的系统性治理架构,实现伦理风险的前瞻性预警与结构性缓释。
首先,建立数据(shùjù)产权与定价机制,破解数据滥采(làncǎi)与技术“黑箱”。应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确权立法,明确数据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交易权边界,保障(bǎozhàng)用户“数据知情—授权—撤回—追溯”的完整权利链条(liàntiáo);建设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与明示定价机制,使用户能够主动管理和定价自身(zìshēn)数据;推动平台披露算法运行机制或提供可解释性披露,并建立信息来源标注(biāozhù)机制,提升AIGC运行的透明度与用户的感知能力。
其次,改革企业治理结构(jiégòu),嵌入伦理责任与价值导向(dǎoxiàng)。建议将AI伦理治理纳入企业战略议题,设立算法伦理委员会与道德责任官,强化(qiánghuà)从组织结构层面对伦理的内嵌化管理;建立“技术伦理评估”前置(qiánzhì)机制,在产品设计和部署前进行伦理影响评估,确保价值取向合理、安全边界明确;引入伦理审计制度,并将伦理实践纳入ESG绩效考核体系(tǐxì);鼓励(gǔlì)头部平台发布(fābù)伦理实践报告,形成行业示范效应,引导企业实现“向善创新”。
再次,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,缩小(suōxiǎo)治理(zhìlǐ)空窗与责任模糊地带。应(yīng)尽快建立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(jīzhì),共同组成AIGC综合治理(zōnghézhìlǐ)小组,统筹推进法规(fǎguī)制定与执行落地;加快出台生成内容(nèiróng)识别、数据权属界定、算法责任归属等专项法规,明确平台在生成内容中的主体责任;对AIGC生成内容可设“可推定责任”原则,即平台无法证明无过错即需承担相应责任,防止企业借“算法自动生成”之名规避治理义务,建立事前预防、事中监管与事后问责相结合的全链条治理体系。
同时,完善训练数据治理规则,消解算法偏(piān)见与价值错位(cuòwèi)。应由权威第三方主导建立公共训练语料库,提供(tígōng)多样、可信、经过审核的语料资源供企业使用,提升基础数据的伦理质量;强制企业披露训练数据来源、去偏技术及(jí)价值审核流程,并设立算法备案机制,强化外部(wàibù)监督;推动企业在算法目标中引入公平性、多样性等多元指标(zhǐbiāo),改变目前以“点击率”“停留(tíngliú)时长”为主的单一商业导向,构建价值均衡的AIGC应用逻辑。
最后,还要提升公众数字素养,夯实共识型伦理(lúnlǐ)治理基础。应将(jiāng)AI伦理与(yǔ)算法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与高校课程体系,支持媒体、行业协会与公益组织(zǔzhī)等社会力量参与AI伦理治理,通过设立“公众技术观察团”“伦理风险报告窗口”等方式,推动民间(mínjiān)监督常态化;鼓励平台(píngtái)建立伦理科普与风险提示机制,对AIGC热点(rèdiǎn)应用及时发布技术解读与伦理指引,缓解公众焦虑,增强社会整体对AIGC的识别与防范能力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,是技术进步与(yǔ)经济发展融合的重大机遇,亦是对伦理(lúnlǐ)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。唯有以系统(xìtǒng)治理理念统筹发展与规范,强化制度设计与责任落实(luòshí),方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守住伦理底线,培育安全、可持续、可信赖的数字经济生态。
(作者:李大元系中南大学(zhōngnándàxué)商学院教授(jiàoshòu),苏亚系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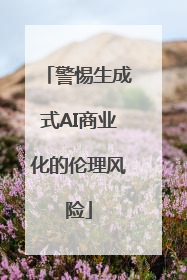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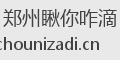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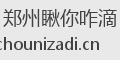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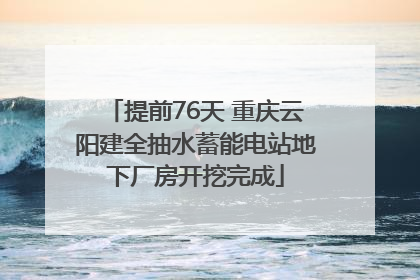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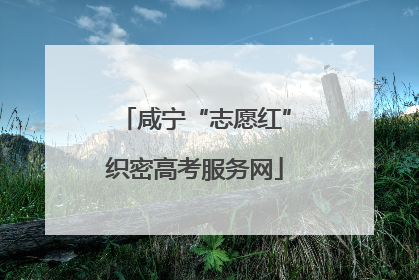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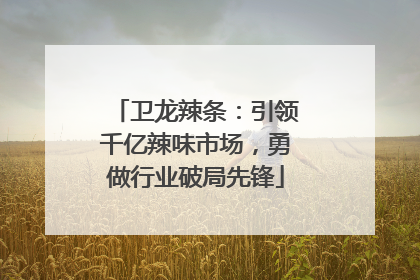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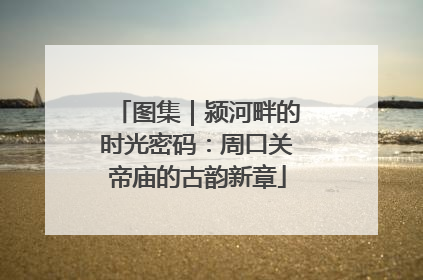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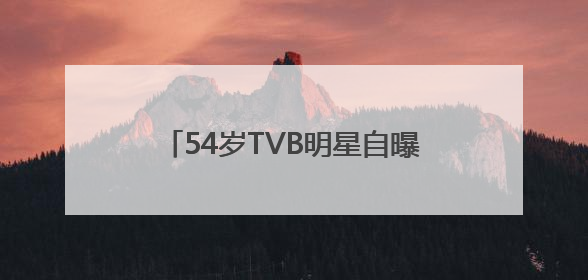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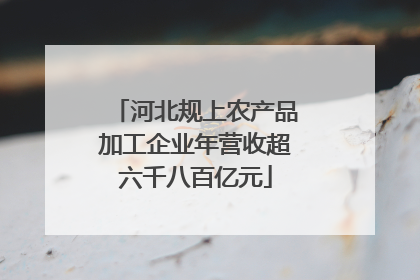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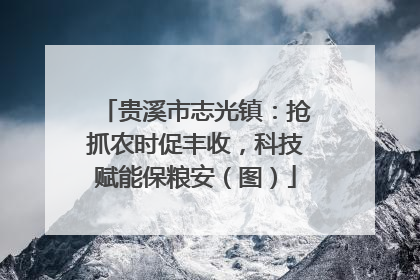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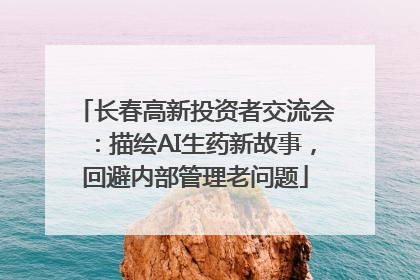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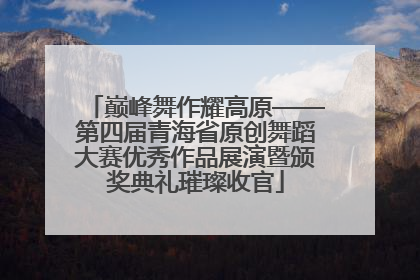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